
翻譯:Erich Sia
困境與展望
許多國家政局受到賄賂的影響,
這並不是什麼秘密,
有些甚至深入各個行政部門,
並且蹂躪老百姓。
只要這些國家依舊脫離世俗,
就不要奢望這些出口國家的寵物貿易會有所改革。
因此唯有寵物進口國才能夠影響局面。
就是得持續且徹底的監控。
對於顯然特別容易滿足且定期放行可疑進口的國家,
例如日本、台灣和泰國(註一),
此事更是應該要做。
尤其是在植物方面在實務上,
以較高分類等級(僅登錄屬名和科名等)的作法,
在高等動物上是無法對準目標的,
因此對於所有的動物活體之商業進口,
都應該防止這種不夠詳盡的作法。
從非 CITES 會員國的進口,
則應當完全中止。
因為這些國家,
更無法擔保永續性的問題,
例如哈薩克-黎巴嫩-日本的聯結關係。

歐盟透過複雜的法令和規範,
設立了一個非常可貴且有效的手段來保育物種。
不管 CITES 會員國的會議決議如何,
自行提高保育等級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例如陸龜屬(Testudo spp.)和薄餅龜(餅乾龜)(Malacochersus tornieri),
雖然是列在 CITES 附錄II內,
在歐盟內則以附錄I來看待。
歐盟採取的這種貿易限制,
更能強化原本的目的。
由於 CITES 要求野生動物的貿易不得危及野外族群的生存,
可是實際上卻如前文所述,
出口國經常提不出"非有害性判定(non-deteriment findings)",
而且/或者以"人工繁殖"的錯誤標示來交易。
歐盟則對於預計要進口的動物,
提出了"非有害性判定"的驗證要求。
中國以大量消費龜類肉品並以烏龜當作傳統醫學的素材,然而寵物貿易對於危及品種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歐盟的科學評估組(SRG, Scientific Review Group)通常每三年召開一次會議,
能夠透過所謂的"負面評價(negative opinion)",
立即禁止歐盟全境的進口。
這種禁令並非針對某物種的所有個體一概適用,
而是結合了原產國、物種和來源(也就是野生或在人工環境內繁殖、出生或養大)等綜合因素。
這種評價會定期的檢討,
任何時間都可能再度改變。
在與出口國進行接觸後,
如果狀況未見改善,
負面評價也可能調整成長期禁令。
遇到這樣的情況時,
擱置進口的法規通常會每年更新一次。
德國聯邦政府的自然保護局內,
就可查詢到歐盟科學評估組針對所有物種的正面和負面評價。
緬甸星龜(Geochelone platynota)的交易量雖然不大,但真正的來源並不清楚。歐盟禁止來自緬甸的野生個體進口。

如果其他的國家能夠採用或發展出這樣的模式,
是最好不過了。
在准許進口前若有標準化的評估,
就不會出現令人髮指的案例,
例如有 3,100 隻薄餅龜以野生捕獲的名義,
從剛果共和國出口了。
然而薄餅龜具目前所知,
卻非該國的原生物種。
也就是所謂的"大宗貿易覆審程序(Significant Trade-Review-Process)",
但其作用與歐盟的流程是無法相提並論的。
一方面是所有參與 CITES 的會員國都是基於自願的,
也可以再度離開組織,
就是說非常難以對會員國施壓。
在另外一方面,
所有的決議都完全在每三年才舉行一次的 CITES 會議中才能決定,
反應的時間極度的緩慢。

舉個 CITES 體系的運作流程的例子,
在 2005 年所舉行的第 21 屆會議中,
大宗貿易覆審程序的動物委員會針對黎巴嫩的希臘陸龜(歐洲陸龜)(Testudo graeca)族群案件展開探討,
但是那個時候黎巴嫩已經宣布希臘陸龜的交易為非法了。
在 2008 年的第 23 屆會議中,
由於黎巴嫩已經不再出口希臘陸龜了,
因此就予以註記結案。
然而此時約旦已經成了重要的出口國。
很不幸的是,
這種裁決的成果並不豐碩,
因為整個程序並未把約旦包含進來。
四趾陸龜(Testudo horsfieldii)每年以穩定的極高數量進行交易,
例如從 2000 至 2008 年每年平均有 68,000 隻。
從 2005 年起此龜就不再受到監控,
因為交易數量雖然很大且穩定,
但數字總是在 CITES 所容許的限額內。
然而到了 2009 年 CITES 卻確認了,
烏克蘭並非四趾陸龜的原產地,
卻從 2000 至 2005 年出口了 150,000 隻四趾陸龜,
況且先前並無看似合理的進口數量。
於是 CITES 此時才展開相關的程序。
歐盟以動物保護為由禁止阿根廷陸龜(Chelonoidis chilensis)進口好幾年的時間,這個禁令現在已經解除,可以再度進口了。

當我們分析貿易的統計資料,
並且見到了如此明顯的以"人工繁殖"來謊報,
只會有一種後果。
只要普遍存在的監控依舊不可能,
陸龜的國際交易就應當包含完整的資料蒐集,
包括群體的移動、繁殖族群的辨認標記(例如拍照建檔),
以及公開所有"人工繁殖"個體進口許可的先決條件,
對於 CITES 附錄II的物種也必須如此。
應該比現今的制度進行更頻繁的調整。
可交易的範圍應該加以明定,
以提供品種保育和動物健康兩者間的折衷作法。
透過宣布可交易的最大尺寸,
能夠排除(或至少降低)野生個體被任意的改變標示;
而固定的最小尺寸也能預防極幼小個體的交易,
以減少運送過程中或飼主購買後沒多久的高死亡率。
除此以外,
同一繁殖農場內應當停止同一品種的不同標示之混用,
否則的話很容易就將個體的來源歸類加以變動,
以因應不同購買國家的需求。
四趾陸龜(Testudo horsfieldii)經常被 CITES 列入大宗貿易覆審程序(Significant Trade-Review-Process),因為牠們以無法想像的數量被人捕捉並進行動物交易。

為了認清問題的嚴重性,
我們不要忘了,
我們目前只論及活的烏龜。
國際寵物交易的受害者,
還包括許多其他的爬蟲、鳥類和哺乳動物,
更別提還有恐怖的生鮮肉品市場,
以及烏龜製品的醫藥貿易。
那麼我們就必須將寵物交易所造成的野生族群迫害,
與危及原生態之間畫上等號關係。
全文完。
原文網址:
http://www.schildkroeten-im-fokus.de/pdf/2010tierhandel.pdf
註一:
CHEN, T.-H., H.-S. CHANG & K.-Y. LUE (2009): Unregulated Trade in Turtle Shells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aiwan. – Chelonian Conservation and Biology 8 (1): 1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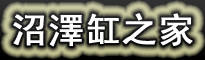

 RSS 訂閱
RSS 訂閱